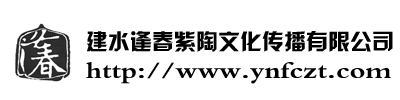心受净土之诱,身坠现世之约。理想向往的崇高和现实境遇的尴尬,逼迫着无聊的叹息。我们穿梭在钢筋混泥土构筑的城市森林里,居住在壮丽高耸的格子房屋中,使用着随时不能离身的机器,吞下明知不是食物的食物,低头不见大地,仰望不见星空,不叹息,又将如何?古人云:“修短随化,终期于尽”,可是,面对着当下这纷杂躁动和急速运转的世界,我们既不能种菊东篱之下,自得于静寂独处的田园生活,又不能彻底地抛弃内心的向往,将儿时的记忆完全忘却;既不能真切的生活在这现实的土地上,又不能感知自然与上天的触动,我们又如何能够“悟言一室之内”亦或“放浪形骸之外”呢?在这人生的逆旅中,它只能如一团篱落的残花,被风时而吹散又聚拢。如果说我们还有希望,那就是随着这花瓣飘落的几粒小小的种子,虽然被冰雪所覆盖,也必将矗立于大地之上,生长在天空之中,这便是内心之诚和艺术之真。
当前中国艺术已深陷严重的功利主义和品格流俗境地,一方面,大量的“艺术家”追从西方当代艺术观念,捧着剽窃所得、哗众取宠的些许图式招摇撞骗,艺术观念和创作语言与西方的相似已到了极其可悲的程度,中国艺术传统的彻底堕落,已成不争的事实。如此下去,非但文脉裂断、风格无存,就连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民族精神的自信都无法可言了。另一方面,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念的土崩瓦解,我国艺术界立马出现了大批所谓的“文人艺术家”,他们进入不了当代艺术的圈子,立马反弹式地大声疾呼“守卫传统”。这类艺术家,妄自尊大、自欺欺人,他们排斥一切西方文化,既不将中国艺术之理路置于全球文化发展的格局下进行深刻探讨,也不潜心研究传统艺术生发和形成的本质,随便买几本画册,乱搞几下笔墨游戏便号称当代“八大”。孰不知,不思进取的复古主义比盲目的崇洋媚外更加可耻。
艺术的价值在于艺术的真实性,是作品所展现的艺术家对生活之本真感悟。艺术的真实性被放弃,艺术创作完全遵从商业利益的话语逻辑,这就给大批投机艺术家创造了舞台,他们不断地进行着你方唱罢我登堂的游戏表演,进而又对真实、高贵之艺术加以可耻地闭搁和漠视,迫使少数诚实、有良知又不甘愿放弃艺术品格的艺术家,在当下不得不呈现出一种无奈的、自我式的,远离话语权的边缘状态。真正的艺术家们,只能以对艺术理想的执着,对人生问题的终极关怀填充现实生活中的茫然。面对现实,他们无法摆脱却不愿归属,只能逃离城市回到乡村,重拾手工的劳作,一边对心灵无法到达之处进行深刻内省,一边艰难的以独立之精神砥砺当代流俗文化趋同。
“艺术是人与自然的相乘”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艺术与工艺的关系。德国艺术史学家格罗塞说:“艺术的起源,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”。文化的起源,来自于物质生产的开始,物质生产的最初形式就是手工艺。实用先于审美,功能先于形式,这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艺术都遵循的发展规律,工艺是文化之根,艺术之母,一切艺术的生发都来自于我们的双手对自然的触碰。没有物质属性的浸润和催发,艺术何以能够出现呢?“形而上者为之道,形而下者为之器”,任何远离了生活之本、自然之真、人性之善的“艺术”,都必将被艺术史所淘汰。工艺从来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,它将自然无穷的眷爱与人类质朴的心灵汇聚一处,使得我们能够倾听到天空的言语,触摸到泥土的芬芳。自然的材料、自发的劳作、纯粹的信仰、质朴的心灵,孕育着工艺诚实、朴素、平和的善良之美。工艺将艺术与自然拉近,艺术之道和工艺之美必然会在自然的某一点上相互交汇。
古城建水,虽地处边疆,但在这里,风俗得以保存,人情更为纯朴,对传统更加敬重,最重要的是这里有陶。要知道,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,要论及人与自然之融通,朴素与高贵之对唔,艺术与工艺之相契,没有什么比陶艺更为传统和适合的了,它是根植于泥土的劳作,同时又是一门伟大的艺术,它被认为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伟大的文明和最重要的造型艺术之一。
在3500余年的建水陶工艺历史中,历代劳作者以朴素之心发现了建水陶的朴素之美。他们在与泥料长期的交往中深谙的它的个性,并智慧的从几十道繁杂的工序中,创造了建水陶“阴刻阳填、无釉磨光”的独特工艺,从而使之成为可将诗文、书法、绘画、篆刻等艺术形式相互融合的一门独立艺术。陶比之纸张更加坚固耐久,比之诗文又能触摸把玩,它不仅可以满足视觉上的审美需求,又能承载触觉上的深度体验。正如陆子刚制玉、陈曼生造壶、西泠八家研印、林清卿雕钮、金西崖刻竹,这些都源自于传统文人对物性之善的直观,器物之美的怀念。
“有涯生待遣,何物性能娱?”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参与建水陶艺术创作的原由。
庚寅年中秋于滇中蒲风书坊